一、前 言
一般认为近代世界的‘世俗化’,已经使宗教大致皆撤离政治领域。但在人类实际的生活中,政治与宗教发生关连的例子仍随处可见,例如教会在东欧民族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回教在中东国家的政治举足轻重,解放神学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影响等等,皆是显例。不过,一般探究政教关系的著作大多集中在基督教、回教方面,亚洲佛教似乎较少受到注意,[1]中国佛教尤然。
例如 Ian Harris 教授于1999年编辑出版的《二十世纪亚洲的佛教与政治》一书,分别探讨了缅甸、泰国、越南、日本……等十个亚洲国家,却缺了最大的国家——中国,该书在序言中说明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流行的政治文化阻碍了佛教的兴盛,之二是‘不易觅得适当的学者来“权威地处理”共产主义下的佛教’。[2]
后一个原因指的是1949年中共建国以后,佛教必须‘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问题,前一个原因指涉的虽是六○年代以来的环境限制,其实应是整个二十世纪(乃至更早),中国社会有着胡适所说的‘非宗教传统’,[3] 初不待无神论的共产党统治之下为然,即在国民政府时期就有著名的1928、1931年的庙产兴学风潮,显示这不只是不良政治、而且是在不利的文化氛围下,佛教受到相当地干扰或破坏。
佛教与传统中国君主专制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既冲突又一致’的基本格局,一致的部分是指佛教作为一股庞大的社会势力,不少帝王为巩固统治秩序而提倡(拉拢)佛教,冲突的部分是指儒佛思想的内在差异、华夷之辨乃至财经因素,在若干朝代都成了迫害佛教的理由。[4] 进入民国之后虽然没有了帝王,上述既冲突又一致的现象仍以不同形式出现。不过若站在佛教的立场,要保护自己、发展自己则已面对不同的环境,对于新时代的民主法治之理念、制度与生活,尤其对教(僧)会团体组织问题,必须有所理解和因应。
号称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政治制度没有相对稳定的型态’、偶而也会‘套用西方政治制度的一种或全部’、‘仍是强烈的封建主义’,[5] 而且经历袁氏复辟、南北分裂等纷扰,比较属于旧时代的延续,1928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则比较接近统一的国家,虽然长期训政、不开放政权,但‘它还是有政府的紊乱,它还是一个有安定希望的社会。’[6] 不过整体而言,1912迄1949年这段期间,中国民主政治未上轨道,佛教与国家社会一样患着虚弱纷扰的毛病,种种改革的倡议,停留在试验、构思的阶段。
在进入本题之前,先就二十世纪上半叶几件相关的大事作一排列整理,俾有助于后续的讨论:[7]
.1910年,杨文会在南京创立‘佛教研究会’,成为日后许多地方性佛学与居士团体的典型。
.1912年4月1日,中华佛教总会筹备处会于上海留云寺召开,选敬安法师为会长,不久全国成立了22个 (省)支部,400多个(县)分部。同年9月敬安等赴北京游说,不顺,猝逝于法源寺,袁世凯不得已令饬内务部核准〈中华佛教总会章程〉。
.1915年6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制定〈寺产管理暂行条令〉,10月袁世凯又发布〈管理寺庙条令〉,宣布取消中华佛教总会,条令内容将寺庙财产处置大权交予地方长官。
.1918年,太虚法师与章太炎、蒋作宾、王一亭等在上海创立‘觉社’。
.1920年2月,《海潮音》创刊。
.1928年3月,南京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提倡庙产兴学,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进而提出具体方案。同年5月,圆瑛、太虚等发起组织‘全国佛教徒代表会议’。
.1929年1月,南京政府内政部颁布〈管理寺庙条例〉21条,内容十分苛刻。4月12日,上海召开全国佛教徒代表会议,决议成立‘中国佛教会 ’,选出执委、监委,圆瑛当选主席。由于太虚与王一亭联名致书蒋介石,南京政府内政部终于准中国佛教会备案,不久,〈管理寺庙条例〉废止,改为较为和缓之〈监督寺庙条例〉13条。
.1930年5月,中佛会于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中国佛教会各省县佛教会组织大纲〉。同年12月,邰爽秋等人成立‘庙产兴学促进会’。
.1931年,中佛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太虚大力批判中佛会并要求改组,在其追随者努力之下,改选结果太虚一系大胜,圆瑛当选常委随即辞职,保守派对改组后的中佛会采不合作态度,抗缴以前认可的经费。太虚拟定保护寺产的建议,经班禅九世在‘国民会议’上提出并获通过,南京政府据此于本年8月1日明令保护寺产,同时,国民党中央党部批准中佛会备案。
.1935年,有七省主管教育人士向南京政府教育部提出接收寺产,充作教育基金的提议,经全国教育会议通过,报内政部。本年7月中佛会召开第七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保守派活动积极,他们提出的新会章获通过,把中央、省、县三级制改为中央、县二级制,太虚退出中佛会,十余省佛教会拒绝改组。
.1936年,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介入调解佛教界内部争端,本年8月圆瑛主持中佛会第七届四次会议,通过恢复三级制。
.1938年4月,中日战争期间,圆瑛等宣布在上海孤岛恢复办公,废止会址迁移重庆的双方前议,在重庆的部分中佛会理监事商决成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由太虚主持,推动僧众救护队、伤兵慰劳队、募捐救济流亡同胞,并与大后方各省县佛教会保持联络。
.1940年1月,圆瑛以老病为由,辞中佛会理事长及灾区救护团团长等职,实则他当时的影响力仅限于江浙沪一隅。
.1943年11月,内政部颁布〈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规定年收益在五万元以上的寺院,由地方政府主持组织的委员会征收其半用于‘公益’,亦即寺庙没有‘自主’兴办公益之权,相当引起佛教界惶恐。
.1944年1月2日,太虚致书蒋介石,要求阻止内政部等所为,否则不能靦颜苟活,‘唯有死路一条’。内政部的〈办法〉终于被搁置。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授与太虚‘胜利勋章’;12月内政部与社会部一起发布训令‘依法组织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指定太虚、章嘉七世、虚云、圆瑛、李子宽、屈映光等九人为委员。
.1947年3月17日,太虚于上海玉佛寺逝世,治丧期间,弟子集议大师色身舍利塔建于奉化雪窦山,法身舍利由印顺负责编纂。同年5月26日,中国佛教会在抗战胜利后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53年6月3日正式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圆瑛当选为会长。
二、代表性思想家的‘政教关系’言论
太虚法师(1889~1947)以倡议佛教的三大革命(教制、教理、教产)著称,而在民主共和时代,欲推动改革务须透过教会团体,所以他认为‘现在国民对于国事皆应有参与政治之行动,实施此种权利,首应有各种团体之组织’,‘出家者为佛教住持僧,在家者为佛教正信会,将此两部联合起来,由县而省,由省而全国,即可构成一整个的佛教团体。’[8] 从本文前言所列的大事纪,可知太虚法师念兹在兹透过建立全国性教会推动改革的努力,终因客观条件限制以及教内派系纷争而归于失败,然而长远来看,他指出的毕竟是正确的方向。
笔者尝略读《太虚大师全书》六十四册,归纳出与政治思想相关的类目为:品评社会主义、含摄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政教关系论。[9] 其中要以‘政教关系论’与现实关系最直接、最深切。太虚鉴于清末民初以来不断发生占寺毁像、提产逐僧或军警驻扎寺宇等情事,政府虽屡布保护法令,‘中枢及各地之首长,虽示提倡赞助,而中下之豪强狃于故习,占寺毁佛提产逐僧之事仍随处随时发现。’[10] 因而除了运用个人影响力局部救火以外,深知佛教本身的改革才是务本之道。他曾主张把汉地八十万僧尼减为四万,以提高僧侣素质,并且把家产的僧寺改为公产的僧团,然而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登记、拣别淘汰、禁止私人剃度以及易滋抗拒的财产改革,非仰赖政府公权力介入不可,但政治力适合作为改革佛教的动力吗?太虚说:‘吾向不视政府为万能,故于整理僧伽制度论,对于寺庙财产,主张以“僧伽基尔特”自为整理而施用于正当之事业。……若拘管于政府之手,则为吾始终反对者也。’[11] 为了解决这种两难,若能在民主法治的通义之下,佛教界有足够的民意代表,制订符合佛教利益的政策,乃是合理的出路,所以太虚法师在战后行宪前夕,才有‘僧伽参政’的提议。
僧伽参政的程度,最高可以到组织佛教政党,至少则是参选民意代表,太虚有感于教内长老缁素‘缄默持重、大多不以为可’,经深思熟虑只好采取后者,即借用孙中山的政权治权理论,主张‘问政而不干治’:
对于有关之民众社团,及乡区自治会议,县参议会,省参议会,国民代表大会,均应参加一份子,为本人同人全民众人议论除苦得乐之办法。但所参预的,以此种议事场所为止,亦即人民政权机关为止;……换言之,只参加选举被选为议员,绝不干求做官,运动作官将——文官武将等。[12]
故而,先前(1936年)太虚曾主张僧尼应参加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也是此种理路下的思考,不过此事引起欧阳竟无致书陈立夫以反对之。欧阳反对的理由大致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内地百万僧尼素质不佳,‘其大多数皆游手好闲,晨夕坐食,诚国家一大蠹虫’,另一是比丘与公民‘各以其类不可混淆’,依《大涅槃经》所说戒:‘比丘不应蓄财、奴役、种植、市易、谈说俗事,又不应亲近国王大臣,此等经律所制,皆是如来所说。’总之出家者应‘行头陀、居兰若’,不应有参加国选之‘慕膻行’。[13] 印顺法师对此有简单的批评:‘欧阳治佛书三十年,偏宗深究,宜其得之专而失之过!’[14] 实则,僧尼素质也许不比一般人好,但不至于比一般人差,参政权的享有乃是平等平等,至于参选国代是不是谈说俗事,是不是等于亲近国王大臣?也有商榷余地。
其次,思想家梁漱溟也是反对佛教为现世所用,对太虚的人生佛教主张不以为然:
似乎记得太虚和尚在《海潮音》一文中要藉着‘人天乘’的一句话为题目,替佛教扩张它的范围到现世生活里来,又仿佛刘仁航和其他几位也都有类乎此的话头,……总而言之,佛教是根本不能拉到现世来用的,若因为要拉它来用而改换它的本来面目,则又何苦如此糟蹋佛教?我反对佛教的倡导,并反对佛教的改造。[15]
梁漱溟认为儒家‘专谈现世生活’,而佛教‘专谈现世生活以外的事’,恐怕不是今日一般佛教学者所能接受的看法。关于出世入世的分疏,印顺法师曾有一段论述:为了全心全力解脱生死而厌弃世间,对宗教的体验来说也许是有用的,但因而对其余一切异常淡漠,对现实人生(家庭、社会、国家)只是消极适应它,这在佛法普及民间而言至少是不够的、不足以适应的,‘面对这种不足以适应社会要求的佛教、圣者,而想起了佛教公认的、释迦佛过去修行的菩萨风范,以及释迦成佛以来为法为人的慈悲与精神,不免要对出世佛法,予以重新的估价。’因而涌现出世而入世的佛教,就是所谓的大乘佛教。[16]
佛教学者张曼涛,就是根据此一大乘佛教的精神,赞扬太虚法师是中国近两千年来的佛教史上,真正表现世出世入之大乘精神的第一人:
大师出于真正佛陀之菩萨心怀,握本执圭,安民安法,故其虽遭遇教内短见之士之反对,却仍然秉着虽万人吾往矣之精神,发表其僧侣参政之论。此在整个大师的思想中,固非一最重要之处,但我们从中国佛教传统的形式以观,则不得不惊奇此乃跃足千波,截断众流之见。由一向隐遁山林寺院之僧,一脚便倡踏入最烦人恼心的民主议会之堂,此设非有其卓越古今之思,真发菩提心者,曷能语此。[17]
印顺法师面对这一篇赞扬太虚的文章,唯恐‘僧伽参政’被当作是否入世、是否大乘精神的唯一判准,遂撰一长文予以批评,还提醒:‘人间一切正行,都可以利益众生,都是菩萨事业,都是摄化道场,都是成佛因行。菩萨利济众生,可以从政而不一定要从政。’[18] 印顺法师的借题发挥,或可使道理更圆融透辟,但张曼涛既已指出僧伽参政之论在整个大师的思想中‘固非一最重要之处’,而且只是‘僧众使用菩萨无量法门中的一法之一’,[19]
其实已经说得够清楚了。
三、从政府档案看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目前中华民国国史馆典藏之《内政部档案》共16421卷,其中有关民国佛教史料约有三百余卷,据学者侯坤宏的整理分析,这批档案除涉及文物维护、佛学院创设、社会救济有关者外,率多与寺产纠纷或庙产兴学引起的交涉有关。原来清末张之洞就有庙产兴学的主张,乃至政策,一九三一年以后可视为第二次庙产兴学风波。所谓风波而不是运动,乃因寺庙方面总是被迫、不是自发,其中要以地方政府包括县长、乡长、保甲强令提拨寺租,强占寺产,乃至毁寺逐僧最为常见,佛教方面则懂得写公文向内政部请愿、抗议,通常内政部方面会行文向地方政府纠正,反对将寺庙财产提充乡镇建设经费,主要考量应在安抚民心或维系起码的法治。
兹从国民政府档案中挑选几个具体的案例,比较深入地探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一) 甘肃省临潭县有一藏传佛教寺院‘嘛呢寺’,其僧纲马昂旺丹主于1924年逝世后,原应由嫡堂孙马辙霄承袭,因该孙年幼故由其师活佛马洛劄丹真江楚暂行代理,17年后(1941)这位代理僧纲圆寂,遂有‘家舍族长并民众大小各代表’再四妥协会商,共选马辙霄正式承袭嘛呢寺僧纲,该寺头目袁得忠等并将此结果向县长立案存查,县长聂迵凡则呈文给甘肃省政府请求‘俯准委任并祈颁发钤记,俾资管理而便统制’,省政府方面‘除令准委任并刊发木质钤记外’,行文内政部 ‘咨请查照备案’。[20] 本案显示县政府是最直接的主管机关,省政府与内政部也分别扮演一定的角色。
(二) 中央政治学校肃州分校于1935年成立后,商同地方当局借用西街武庙三义庙药王庙旧址,稍加修葺开学上课,后来学生班次增多,教室宿舍不敷分配,须扩充校址,乃呈请酒泉县政府按征用民地手续办理,但酒泉钟楼寺认为其寺产香火地二十余亩于1940年11月被该校‘恃强占用’,曾于1941年提起诉讼,经酒泉地方法院、甘肃高等法院第四分院判决所有权归钟楼寺,而1940年12月20日内政部地政司致礼俗司的一份公文指出,有关肃州分校用地归还钟楼寺问题,征收土地兴办学校原则并不违法,但肃州分校‘为直接承受中央管辖监督之学术机构’,依土地法第338条规定应由行政院核准,地价之补偿亦应依第377条之规定办理。不过,经法院判决之后该校仍逾限不还,于是1942年9月8日中国佛教会酒高安敦玉金鼎七县市分会乃电请重庆内政部‘俯准依法转咨归还或饬由该校在该县市区外照亩另购田地交还,以维产权,并请赔偿损失。’[21] 本案牵涉政府间(或政党间)争议,寺庙方面且能采取司法途径,惟该校仍逾限不还,可见司法的权威在当时仍隐而不彰;至于中国佛教会该‘七县市分会’请求内政部出面处理,结果如何限于资料不得而知。
(三) 河南省新蔡县金粟寺,原系清康熙年间宋祖法氏所捐赠之土地房屋改建而成,历经购地扩充颇有规模,但同治年间宋氏子孙企图‘化寺为祠’,强在寺内悬挂宋氏祠堂匾额一面,每年春秋岁时藉着扫祭而要求寺僧供应酒食,若干地方士绅不以为然;1929年宋氏族裔有一名垣忠号英俦者,担任河南省党部委员,乃乘省令‘废庙兴学’之际运作将金粟寺原有田产二千亩拨出一千五百亩筹办私立诞文小学,1940年12月20日该寺住持僧祥云透过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由佛教会理事太虚具名)向内政部行文要求保护寺产,翌年1月9日内政部咨请河南省政府‘查明核办、并希见复’,同月21日又有新蔡县公民刘擎伦等为宋垣忠‘藉兴学名义狡占金粟寺’,呈文内政部‘请饬彻查’,1941年6月2日河南省政府为该省新蔡县金粟寺纠纷回复内政部,所做的处置似乎对金粟寺不利:所有权确定问题属司法范围、1500亩给诞文小学之事照旧、寺僧祥云既然挑拨生事准予驱逐。不过,1942年3月又有新蔡县公民代表张山甫等向内政部呈请查办宋氏家族企图侵占金粟寺庙产的公文,[22] 可见寺院方面除了有佛教会的奥援,也需要一定的社会力(信众)的支持,才可能与省县政府做多年的拔河。
(四) 太虚法师曾经对中国佛教寺院之家族化、子孙化现象不以为然,但单凭佛教自身的力量势难改革,所以太虚针对裁汰僧侣、提升素质的事认为‘非政府主管机关以政治力量执行,亦难睹其成效。’[23] 太虚的期待似非全然空想,而有部分的事实基础。例如1936年9月11日,江苏省政府第1855号训令(摘录):‘令镇江县政府督饬佛教会迅速慎选适当之僧,即日到庵(镇江焦山碧山庵)接管,凡与岫奇有关之法派不得被选,以惩传子传孙之恶习,而树十方常住之先声。’镇江佛教会果然改派定慧寺僧玉泉为住持,碧山庵方面则有退居和尚柳溪等补呈文件,谓该寺向以薙度法派相传,不采选贤制度,例如柳溪继承善微,岫奇接任柳溪。此次岫奇因案去职,9月12日宝莲接任住持亦循此传统,而9月18日镇江佛教会所派定慧寺僧玉泉,并非碧山庵薙度法统,自不能接充碧山庵住持,故于1936年10月30日向内政部提起诉愿;该诉愿人亦无继承资格;同年9月20日柳溪提起再诉愿谓吸食鸦片系遭人挟嫌诬报、不能作为论据;其间由于岫奇、宝莲二人先后呈称本件诉愿案系假冒名义,声明无效,柳溪遂以单独名义表示不服提起再诉愿,内政部于1937年11月1日作成驳回之决定书,就从程序上认为‘无论原处分之内容有无违法或不当情事,与再诉愿之权益并无关系,更无损害之可言。’[24] 本案显示,省政府根据某种资讯和理念,即可训令县政府督饬县佛教会,改变某个寺院的住持,虽然形式上仍经过佛教会或可免除妨碍宗教自由之讥,但政治力强势介入的痕迹明显可见,而僧人柳溪懂得以诉愿、再诉愿的方法维护自己的利益,可以令人感受到中国佛教在1930年代的某种‘现代性’。
四、从《海潮音》杂志看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1918年太虚法师在上海创办‘觉社’,作为其改革佛教的据点,当时出版《觉社丛刊》季刊计有五期,为配合弘法需要,于1920年2月改为《海潮音》月刊,这份刊物随着时局变迁曾在上海、武昌、重庆等不同地方编辑出版,历经善因、满智、法舫、芝峰、福善、尘空、大醒等等不同法师与居士负责编务,1949年迁移台湾继续出版,‘销数不过二千多份,可是读者却遍满了各省市及南洋各处’,[25] 可说是中国佛教迄今为止‘历史最久’的一份刊物,‘相当于一部近代佛教史,为佛教留下完整的纪录’。[26]
1948年负责《海潮音》编务的大醒法师曾说:‘我们(太虚)大师的两大慧命事业,一是武昌佛学院,二是《海潮音》月刊。(法)舫法师……既主持母院约近十载,同时他又为本刊主编有三次之多……。’[27]《海潮音》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反映了太虚法师及其徒众的改革佛教事业,记载了数十年中国佛教的各种动态,自然可以从中看到佛教与政治的若干关系。
首先,来自各地的讯息显示,地方政府与佛教寺院或佛教会互动的情形不一,但觊觎庙产的企图相当普遍。例如1929年安徽省佛教会快邮代电:安庆市政筹备处拟订抽收本市僧道唪经‘迷信捐’章程,呈奉省府第94次委员会谈话会议议决照准,定本年12月1日开始征收;省佛教会遂决议一致反对,自12月1日一律停止应赴三日以示消极抵制,一面请愿省府覆议收回成命,一面呈请全国佛教会,转呈国民政府明令制止。[28] 又如1947年湖北省政府议决酌提庙产收益为教育经费,中佛会认为显与〈监督寺庙条例〉抵触,请内政部转咨撤销,省政府于10月21日发出公函谓:‘自应照办。除分令各县市政府将原经收管之寺庙财产一律发还,并依监督寺庙条例第十条之规定,商得各该寺庙住持僧之同意,将财产收益酌提一部兴办公益慈善事业……’。[29]
再如,1948年浙江定海、镇海县政府根据县参议会之议决,设经忏捐征收所,强迫佛教寺庵缴经忏捐;其实此捐早经中佛会于1930年呈奉国民政府批交行政院令行内政部,请转咨饬令撤销。[30]《海潮音》作为一份佛教刊物,除了记载、传达这类讯息,也会发出批判之声,例如针对1948年3月5日报载上海市参议会议决对于该市寺庙‘得由主管机关会同民意机关及地方公正士绅组织委员会整理之’,上海寺佛教分会认为‘显有侮视教会、侵犯宗教尊严,……殊与宪法相抵触。’大醒法师遂发表文章称许这样的驳论,还说‘今后正是实施宪政的时代了,宪法上给予我们有许多应享的自由权利,我们僧侣应该要自己争取!’[31]
不过,如果根据以上的事例,即作成‘民国佛教总是受到地方政府的压迫剥削’的单一结论,恐亦不合史实。例如湖南省宁乡有一大沩山密印寺(沩山寺),原有山田3,700余亩,以放佃收租作为寺院的收入来源,惟寺僧只有完粮收租之权,并无退佃之权,若佃房不种可自觅替人,寺僧不得干涉或收回,此制自唐代以来一无变更;1930年《海潮音》关于沩山寺有一则记载谓:佃户多至六百余家,人数既众良莠不齐,每多欺凌寺僧,欠租抗粮、因循积习,终于酿成 1918年‘匪佃’放火戮僧之惨祸。沩山寺僧所能采取的对策,除了谆谆告诫、晓以因果,或召集团甲转谕各佃不得借端刁抗以外,还可以向宁乡县长刘裔彬求援:‘以后该沩山佃户如仍有短租情事,一经该寺僧呈诉,即请拘案追缴,刘县长亦允依法维持。’[32] 可见,佛教寺院也有仰赖地方政府‘保护’以维持生计的一面。
从中央政府的层面看,民国时期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确有一定程度的亲佛环境,一位作者如此描述:‘现政府中之重要领首,皆多信佛。如国民政府主席林子超氏,即笃信佛教;司法院长居觉生氏,亦甚信佛。即军事领袖蒋介石氏,亦极爱护佛教。’[33] 其中,所谓蒋介石爱护佛教,应与太虚法师有关,即1927年9月蒋氏电邀太虚游奉化雪窦寺,两人长谈竟日、相偕游千丈岩,时逢中秋赏月,太虚又为蒋氏夫妇(蒋经国之母)等略说心经大意。印顺法师就此评论道:‘国民政府下之佛教,得以从狂风暴雨中复归安定,得以泄沓混日,确与此夜此人有关。’[34] 再者,1932年10月8日,太虚应蒋氏延请,任奉化雪窦寺住持,行进院礼,[35] 此后数年太虚在该寺开讲《出生菩提心经》、《弥勒上生经》、《解深密经》等多部经典,并曾设药师法会,祝蒋五秩之庆。[36] 此外,中高层的军政人物也不乏护持佛教的事例,如1932年世界佛学苑汉藏院正式开学,由重庆佛学社向国民革命军第廿一军司令部‘呈请拨款’,军长刘湘准于省教育经费项下,按月拨助洋600元,以资进行;[37] 同年的《海潮音》也曾记载,武昌佛学院董事会欢迎徐督办克成、夏司令灵柄为‘院护’云云。[38]
佛教界基于信仰的立场以及自身能力考量,曾在中日战争期间组织僧侣救护队,参与‘救死护生’,[39] 平常则启建法会以祈求国泰民安,例如1931年11月26日迄1932年5月25日,长沙启建半年的水陆道场,以超渡全国阵亡将士;[40] 1932年10月21日,北平雍和宫启建三天的时轮金刚法会,虽尝被讥为‘经咒救国’,但法舫法师认为这是1932年全国佛教五项重要的成绩之一。[41]
不过,透过私人情谊或以法会消灾祈福,不足以构成制度化的、现代化的政教关系。尤其国共内战方殷,共产党势力日趋壮大之际,前述坐拥田产收取地租的寺院经济模式,自然受到教内有识之士的检讨,1948年善因、大醒就撰文呼吁全国各寺院,只要有田土可耕、有山林可植,就应添些农具耕牛,收回土地自耕,既可不受饥饿之苦、不受外界之摧残,又可加政府之保障,‘但应留点慈念,对于每一佃农所耕之田,只宜收回半数或一部份来自耕,毋使旧佃完全失业,以符佛心。 ’‘与其替斋主做经忏,不如自食其力。’[42] 另一位作者也说:‘僧伽应根据《郁单越国经》所说的佛教的社会主义或民生主义,想出切实的办法,付诸实行,以求达到目的。’[43] 对于国共内战,则有人从佛教的观点提出批判:‘谁都知道内战发生的原因,是两个党因为互争政权而生起的。’‘双方都把党的利益高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都在驱赶着善良的人民做着民族自戕的蠢事。’内战发生的主因既然是两党的自私性,‘去私’便是和谈成功的首要条件。[44] 道理虽然讲得不错,但是对于客观决定的结构、江河日下的局势,显然无济于事。
五、讨论与结语
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在神学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解放神学家认为,神学主要是要对实际的生活提出批判、反应与思考,他们使用的方法可归纳为四点: (一) 主张‘历史的实践’,(二)‘历史的情况’是神学思考的出发点,有别于过去以圣经或启示为出发点,(三) 藉助社会科学的方法来了解历史实际情况,(四) 神学思考必须采用某种意识型态,一般解放神学家率皆主张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包括采用依赖理论(theory of
dependence)来了解拉丁美洲的实况。以上第四点最容易引起争议,解放神学家的理由是:信仰必需意识型态来作媒介,否则会与历史实况脱节、会成为死的信仰。[45] 然而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神学思考如何与无神论相协调?会不会喧宾夺主?不论是选择性地使用圣经,或选择性地采用马克思主义,选择的根据何在?俱是问题。
佛教方面不容易找到可与解放神学相比拟的思想,勉强说,泰国的佛使比丘(1906-1993)有接近之处,佛使认为宗教与政治有基本的关连,真正的政治是用来对治邪知、邪见、贪爱烦恼和类似的弊病;社会科学本质上就是一种道德,因为它的目的是解决社会所有的问题,使社会和谐、平衡。佛使还认为理想的民主政治是‘如法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它必须限制个人自由,必须采用‘独裁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例如阿育王的政治制度就是一种全然‘独裁的’社会主义,他驱逐僧伽中的外道人士,并严格要求所有阶层百姓的行为都要端正,他是一位为全体福利着想的君主。[46] 虽然佛使比丘对社会主义的定义特殊,把它当作相对于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而言,或有自圆其说的可能,但在二十世纪鼓吹独裁的方法,毕竟不合时宜。
不过,解放神学家所谓‘历史的情况’、‘社会科学的方法’则很值得重视,本文企图从国民政府的内政部档案,以及从《海潮音》月刊入手,就是要究明 1912~1949年之中国的历史实况。大率归纳而言:(一) 不论在清末、北洋政府或南京政府时代,都有庙产兴学或课征迷信捐、经忏捐的倡议,可见在政治因素之外,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容忽视;(二) 比较而言,地方政府的苛扰比中央政府严重,中央方面的亲佛环境则是因为首长信佛或如太虚、蒋介石的私人关系,并非制度性的保障;(三) 《海潮音》也曾记载,县长派兵协助佛教寺院向佃户收租的情形,可见不能做成民国时期‘政府迫害佛教’的简化结论;(四) 佛教方面常举办护国息灾法会、超渡阵亡将士法会,抗日战争期间努力发挥‘救死护生’的角色,整体而言是采取支持(拥护)政府的立场;[47] (五) 佛教徒已经懂得透过立法、透过组织教会,甚至个别地以诉愿、再诉愿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惟全国性的教会频生波折,部分的因素来自教内的派系纷争。此外,关于僧伽参政的问题,虽曾受到教内教外人士的质疑,笔者认为主要的困难不在于理论、不在于有否经说的依据,而在于实际上佛教界有没有整合的机制以提出具代表性的候选人?在于佛教界对当下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诸问题能提出什么‘如法的’主张?
理论上孰为理想的政教关系,近年来已有学者强调‘政教制衡’而非‘政教分立(离)’,更非‘政教合一’,笔者同意政教制衡的确比较切合实际且符合民主之理,亦即政治与宗教之间可以互相支持也可以互相反对,只要遵守‘不过份连结’(non-excessive
entanglement)和‘非歧视性’(non-discrimination)两个原则即可。[48] 昔日太虚法师关于淘汰僧尼、整建僧会的目标曾经寄望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今日看来当知不切实际,而全国性的教会也不足以作为佛教现代化的首要指标,观乎今日中国大陆虽有‘中国佛教协会’,不见得即能发挥佛教的主体性,很多时候只是政治控制的一环。可见佛教现代化的问题,也要放在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来看,佛教毕竟是国家社会的一环,理想的政教关系只有在政治民主、社会健全的环境下才可能产生。因而佛教界对于国家社会的民主进步、公平正义如果不能扮演推手,至少也不应是旁观者或是向下拉扯的角色,所以个人认为,太虚法师不避政僧之讥,勇于对社会主义、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乃至具体的公共事务发言,犹应是今日佛教徒应该重视的榜样。最后,已故佛教学者傅伟勋教授的一段话,很适合作为本文的结尾:
我衷心盼望现代佛教徒以及佛教团体能够更积极地参与世间世俗的政治活动与社会工作,把大乘佛法的菩萨道精神真正带到我们人间的日常生活之中。佛教团体必须能够提出有助于社会福利与进步的建设性主张与措施,必须敢于提出有佛法根据的政见,也必须好好利用时机,在民主自由而多元开放的公开讨论条件下,正面提出具有说服力的佛教看法。……无论如何,奉持佛法的现代人不能再像过份保守的传统佛教那样,隔断佛法与世法,漠视世法,只管佛法。真正的佛法必须在从事于世法的改善转化的奋斗过程当中彰显出来,这是根据二谛中道产生的关涉佛教伦理本身应有的实践态度。[49]
【注释】
[1] 近年中国大陆出版品则有改变的现象,例如赵匡为主编,《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教关系》(第一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年),已处理到日、韩、泰、缅等国。又如宋立道,《神圣与世俗:南传佛教国家的宗教与政治》(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综论佛教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关系。
[2] Ian Harris, ed., Buddhism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1999), Preface, p. viii.
[3] 或称‘薄弱的宗教心’,见胡适,〈三论信心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07号(1934年7月1日),页2-6。
[4] 用美国学者史丹利.外因斯坦(Stanley
Weinstein)的话说,唐朝早期的帝王对佛教采取的是‘权宜的护持伴随着渐趋严峻的控制手段’。见氏着,释依法译,《唐代佛教:王法与佛法》(台北:佛光文化公司,1999年),页6。
[5] 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75。
[6] 李时友,〈中国国民党训政的经过与检讨〉,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八辑‘十年建国’(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页24。
[7] 以下大事整理自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页35-56;印顺,《太虚大师年谱》(台北:正闻出版社,1992年修订一版)。
[8] 太虚法师,〈建设适应时代之中国佛教〉,《太虚大师全书》(台北:太虚大师全书影印委员会,1956年初版,1970年再版),第35册,页4。
[9] 陈仪深,〈太虚法师的政治思想初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期(1990年6月),页279-298。
[10] 太虚法师,〈精诚团结与佛教之调整〉,《全书》第34册,页634。
[11] 太虚法师,〈上海市庙产注册事件〉,《全书》第34册,页641、642。
[12] 太虚法师,〈僧伽与政治〉,《全书》第35册,页180-183。
[13] 欧阳竟无,〈辨方便与僧制〉,收入洪启嵩、黄启霖编,《欧阳竟无文集》(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页219-228。
[14] 印顺,《太虚大师年谱》,页406。
[15]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台北:问学出版社,1977年),页210-211。
[16] 印顺,〈谈入世与佛学〉,收入《无诤之辩》(台北:作者出版,1976年),页182-183。
[17] 张曼涛,〈太虚大师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之地位及其价值——为纪念虚大师上生二十周年而写〉,收入氏着《佛教思想文集》(台北:狮子吼杂志社,1969年),页212-230。
[18] 印顺,〈谈入世与佛学〉,同前,页200。
[19] 详见张曼涛,〈读‘谈入世与佛学’后〉,前揭书,页154-211。[20] 国史馆藏《内政部档案》,(档号待查):甘肃省政府咨(内政部查照准临潭县政府)请委任马辙霄为临潭县嘛呢寺僧纲(1941年2月20日)。
[21] 国史馆藏《内政部档案》,128/1602:行政院交议有关中国佛教会酒高安敦玉金鼎七县分会代电请饬令中央政治学校肃州分校归还酒泉钟楼寺地产案(1940年12月13日);128/1605:中国佛教会酒高安敦玉金鼎七县分会电请依法转咨饬还钟楼寺产(1942年9月8日)。
[22] 国史馆藏《内政部档案》,档号待查:河南省政府为该省新蔡县金粟寺纠纷咨内政部(1941年6月2日);河南省新蔡县公民代表张山甫等呈请查办该县宋氏家族企图侵占金粟寺庙产乙案(1942年3月)。
[23] 太虚法师,〈建设现代化中国佛教谈〉,《全书》第33册,页278。
[24] 国史馆藏《内政部档案》,128/1621:江苏镇江焦山碧山庵僧人柳溪等不服江苏省府所为行政处分提起诉愿(1936年10月16日);(档号待查):内政部决定驳回江苏镇江焦山碧山庵住持纠纷再诉愿案(1937年11月1日)。
[25] 大醒,〈为本刊迁移台湾讲几句话〉,《海潮音》第三十卷第六期(1949年6月)。
[26] 于凌波,《中国近代佛门人物志》(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页245。
[27] 大醒,〈欢迎法舫法师归国〉,《海潮音》第廿九卷第六期(1948年6月)。
[28] 〈安徽省佛教会快邮代电〉,《海潮音》第十一卷第一期(1930年1月)。
[29] 〈中佛会会报〉,《海潮音》第廿九卷第一期(1948年1月)。
[30] 《海潮音》第廿八卷第十二期(1947年12月)。又参见大醒,〈镇海发生县税稽征人员捣毁寺庵事件〉,《海潮音》第廿九卷第十一期(1948年11月)。
[31] 大醒,〈我们不承认有干涉寺政寺产之任何名义的组织〉,《海潮音》第廿九卷第五期(1948年5月)。
[32] 〈陈委员严华为沩山寺自呈覆省政府及民政厅文〉,《海潮音》第十一卷第二期(1930年2月)。同期有〈罘月致太虚函〉谓县政府派兵四员协助催租,也是保护佛教云云。
[33] 谭云山,〈中国佛教现状〉,《海潮音》第十五卷第九期(1934年9月)。
[34] 印顺,《太虚大师年谱》,页240。
[35] 同上注,页347。另据谈玄法师(1937年奉太虚之命赴雪窦寺代理)的说法,并非‘应蒋氏延请’,而是1932年雪窦寺住持朗清以太虚与最高领袖相友善,遂率寺众并商同诸山及溪口镇绅,公请太虚来寺住持。见国史馆藏,《内政部档案》,128/1686:谈玄僧呈请驱逐劣僧案。
[36] 印顺,《太虚大师年谱》,页414。
[37] 《海潮音》第十三卷第八期(1932年8月)。
[38] 《海潮音》第十三卷第四期(1932年4月)。
[39] 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276。又,有关中国佛教在抗战期间的表现,详见乐观法师,《中国佛教近代史论集》(台北:作者出版,1978年),页23-99。
[40] 《海潮音》第十三卷第六期(1932年6月)。
[41] 《海潮音》第十三卷第十二期(1932年12月)。另外四项是宋版藏经影印、世界佛学苑设立、河南省佛教学苑设立、重兴洛阳白马寺。
[42] 善因、大醒,〈赞成僧作自耕农〉,《海潮音》第廿九卷第十二期(1948年12月)。
[43] 伍薏农,〈我们往那里住?——36年在厦门寿山岩讲〉,《海潮音》第廿九卷第四期(1948年4月)。
[44] 石孚,〈从无我大悲的观点看和平运动〉,《海潮音》第三十卷第三期(1949年3月)。
[45] 慕理诺(Miguez-Bonino)等着,《基督教与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台北:台湾神学院,1995年),廖涌祥牧师引言,页15-29。
[46] 佛使比丘(Buddhadàsa Bhikkhu)着,香光书乡编译组译,《法的社会意义》(嘉义:香光书乡出版社,1996年),页86、87、90、100。
[47]
曾有学者归纳,宗教团体对政府采取的态度可有四种类型:支持,中立,以社会为立场、为社会作见证,公然对抗。无疑,民国时期的佛教属第一种。参见Murray
A. Ribinstein, ' Patterns of Church and State Relations in Modern Taiwan ', 收入《中国近代政教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淡江大学,1987年),pp.359-374。
[48] 参见郭承天,《政教的分立与制衡》(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2001年)。
[49] 傅伟勋,〈(大乘)佛教伦理现代化重建课题试论〉,收入氏主编《从传统到现代——佛教伦理与现代化社会》(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年),页233-250。
一般认为近代世界的‘世俗化’,已经使宗教大致皆撤离政治领域。但在人类实际的生活中,政治与宗教发生关连的例子仍随处可见,例如教会在东欧民族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回教在中东国家的政治举足轻重,解放神学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影响等等,皆是显例。不过,一般探究政教关系的著作大多集中在基督教、回教方面,亚洲佛教似乎较少受到注意,[1]中国佛教尤然。
例如 Ian Harris 教授于1999年编辑出版的《二十世纪亚洲的佛教与政治》一书,分别探讨了缅甸、泰国、越南、日本……等十个亚洲国家,却缺了最大的国家——中国,该书在序言中说明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流行的政治文化阻碍了佛教的兴盛,之二是‘不易觅得适当的学者来“权威地处理”共产主义下的佛教’。[2]
后一个原因指的是1949年中共建国以后,佛教必须‘与社会主义相协调’的问题,前一个原因指涉的虽是六○年代以来的环境限制,其实应是整个二十世纪(乃至更早),中国社会有着胡适所说的‘非宗教传统’,[3] 初不待无神论的共产党统治之下为然,即在国民政府时期就有著名的1928、1931年的庙产兴学风潮,显示这不只是不良政治、而且是在不利的文化氛围下,佛教受到相当地干扰或破坏。
佛教与传统中国君主专制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既冲突又一致’的基本格局,一致的部分是指佛教作为一股庞大的社会势力,不少帝王为巩固统治秩序而提倡(拉拢)佛教,冲突的部分是指儒佛思想的内在差异、华夷之辨乃至财经因素,在若干朝代都成了迫害佛教的理由。[4] 进入民国之后虽然没有了帝王,上述既冲突又一致的现象仍以不同形式出现。不过若站在佛教的立场,要保护自己、发展自己则已面对不同的环境,对于新时代的民主法治之理念、制度与生活,尤其对教(僧)会团体组织问题,必须有所理解和因应。
号称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政治制度没有相对稳定的型态’、偶而也会‘套用西方政治制度的一种或全部’、‘仍是强烈的封建主义’,[5] 而且经历袁氏复辟、南北分裂等纷扰,比较属于旧时代的延续,1928年以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则比较接近统一的国家,虽然长期训政、不开放政权,但‘它还是有政府的紊乱,它还是一个有安定希望的社会。’[6] 不过整体而言,1912迄1949年这段期间,中国民主政治未上轨道,佛教与国家社会一样患着虚弱纷扰的毛病,种种改革的倡议,停留在试验、构思的阶段。
在进入本题之前,先就二十世纪上半叶几件相关的大事作一排列整理,俾有助于后续的讨论:[7]
.1910年,杨文会在南京创立‘佛教研究会’,成为日后许多地方性佛学与居士团体的典型。
.1912年4月1日,中华佛教总会筹备处会于上海留云寺召开,选敬安法师为会长,不久全国成立了22个 (省)支部,400多个(县)分部。同年9月敬安等赴北京游说,不顺,猝逝于法源寺,袁世凯不得已令饬内务部核准〈中华佛教总会章程〉。
.1915年6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制定〈寺产管理暂行条令〉,10月袁世凯又发布〈管理寺庙条令〉,宣布取消中华佛教总会,条令内容将寺庙财产处置大权交予地方长官。
.1918年,太虚法师与章太炎、蒋作宾、王一亭等在上海创立‘觉社’。
.1920年2月,《海潮音》创刊。
.1928年3月,南京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提倡庙产兴学,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进而提出具体方案。同年5月,圆瑛、太虚等发起组织‘全国佛教徒代表会议’。
.1929年1月,南京政府内政部颁布〈管理寺庙条例〉21条,内容十分苛刻。4月12日,上海召开全国佛教徒代表会议,决议成立‘中国佛教会 ’,选出执委、监委,圆瑛当选主席。由于太虚与王一亭联名致书蒋介石,南京政府内政部终于准中国佛教会备案,不久,〈管理寺庙条例〉废止,改为较为和缓之〈监督寺庙条例〉13条。
.1930年5月,中佛会于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中国佛教会各省县佛教会组织大纲〉。同年12月,邰爽秋等人成立‘庙产兴学促进会’。
.1931年,中佛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太虚大力批判中佛会并要求改组,在其追随者努力之下,改选结果太虚一系大胜,圆瑛当选常委随即辞职,保守派对改组后的中佛会采不合作态度,抗缴以前认可的经费。太虚拟定保护寺产的建议,经班禅九世在‘国民会议’上提出并获通过,南京政府据此于本年8月1日明令保护寺产,同时,国民党中央党部批准中佛会备案。
.1935年,有七省主管教育人士向南京政府教育部提出接收寺产,充作教育基金的提议,经全国教育会议通过,报内政部。本年7月中佛会召开第七届全国佛教徒代表大会,保守派活动积极,他们提出的新会章获通过,把中央、省、县三级制改为中央、县二级制,太虚退出中佛会,十余省佛教会拒绝改组。
.1936年,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介入调解佛教界内部争端,本年8月圆瑛主持中佛会第七届四次会议,通过恢复三级制。
.1938年4月,中日战争期间,圆瑛等宣布在上海孤岛恢复办公,废止会址迁移重庆的双方前议,在重庆的部分中佛会理监事商决成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由太虚主持,推动僧众救护队、伤兵慰劳队、募捐救济流亡同胞,并与大后方各省县佛教会保持联络。
.1940年1月,圆瑛以老病为由,辞中佛会理事长及灾区救护团团长等职,实则他当时的影响力仅限于江浙沪一隅。
.1943年11月,内政部颁布〈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规定年收益在五万元以上的寺院,由地方政府主持组织的委员会征收其半用于‘公益’,亦即寺庙没有‘自主’兴办公益之权,相当引起佛教界惶恐。
.1944年1月2日,太虚致书蒋介石,要求阻止内政部等所为,否则不能靦颜苟活,‘唯有死路一条’。内政部的〈办法〉终于被搁置。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授与太虚‘胜利勋章’;12月内政部与社会部一起发布训令‘依法组织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指定太虚、章嘉七世、虚云、圆瑛、李子宽、屈映光等九人为委员。
.1947年3月17日,太虚于上海玉佛寺逝世,治丧期间,弟子集议大师色身舍利塔建于奉化雪窦山,法身舍利由印顺负责编纂。同年5月26日,中国佛教会在抗战胜利后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53年6月3日正式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圆瑛当选为会长。
二、代表性思想家的‘政教关系’言论
太虚法师(1889~1947)以倡议佛教的三大革命(教制、教理、教产)著称,而在民主共和时代,欲推动改革务须透过教会团体,所以他认为‘现在国民对于国事皆应有参与政治之行动,实施此种权利,首应有各种团体之组织’,‘出家者为佛教住持僧,在家者为佛教正信会,将此两部联合起来,由县而省,由省而全国,即可构成一整个的佛教团体。’[8] 从本文前言所列的大事纪,可知太虚法师念兹在兹透过建立全国性教会推动改革的努力,终因客观条件限制以及教内派系纷争而归于失败,然而长远来看,他指出的毕竟是正确的方向。
笔者尝略读《太虚大师全书》六十四册,归纳出与政治思想相关的类目为:品评社会主义、含摄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政教关系论。[9] 其中要以‘政教关系论’与现实关系最直接、最深切。太虚鉴于清末民初以来不断发生占寺毁像、提产逐僧或军警驻扎寺宇等情事,政府虽屡布保护法令,‘中枢及各地之首长,虽示提倡赞助,而中下之豪强狃于故习,占寺毁佛提产逐僧之事仍随处随时发现。’[10] 因而除了运用个人影响力局部救火以外,深知佛教本身的改革才是务本之道。他曾主张把汉地八十万僧尼减为四万,以提高僧侣素质,并且把家产的僧寺改为公产的僧团,然而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登记、拣别淘汰、禁止私人剃度以及易滋抗拒的财产改革,非仰赖政府公权力介入不可,但政治力适合作为改革佛教的动力吗?太虚说:‘吾向不视政府为万能,故于整理僧伽制度论,对于寺庙财产,主张以“僧伽基尔特”自为整理而施用于正当之事业。……若拘管于政府之手,则为吾始终反对者也。’[11] 为了解决这种两难,若能在民主法治的通义之下,佛教界有足够的民意代表,制订符合佛教利益的政策,乃是合理的出路,所以太虚法师在战后行宪前夕,才有‘僧伽参政’的提议。
僧伽参政的程度,最高可以到组织佛教政党,至少则是参选民意代表,太虚有感于教内长老缁素‘缄默持重、大多不以为可’,经深思熟虑只好采取后者,即借用孙中山的政权治权理论,主张‘问政而不干治’:
对于有关之民众社团,及乡区自治会议,县参议会,省参议会,国民代表大会,均应参加一份子,为本人同人全民众人议论除苦得乐之办法。但所参预的,以此种议事场所为止,亦即人民政权机关为止;……换言之,只参加选举被选为议员,绝不干求做官,运动作官将——文官武将等。[12]
故而,先前(1936年)太虚曾主张僧尼应参加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也是此种理路下的思考,不过此事引起欧阳竟无致书陈立夫以反对之。欧阳反对的理由大致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内地百万僧尼素质不佳,‘其大多数皆游手好闲,晨夕坐食,诚国家一大蠹虫’,另一是比丘与公民‘各以其类不可混淆’,依《大涅槃经》所说戒:‘比丘不应蓄财、奴役、种植、市易、谈说俗事,又不应亲近国王大臣,此等经律所制,皆是如来所说。’总之出家者应‘行头陀、居兰若’,不应有参加国选之‘慕膻行’。[13] 印顺法师对此有简单的批评:‘欧阳治佛书三十年,偏宗深究,宜其得之专而失之过!’[14] 实则,僧尼素质也许不比一般人好,但不至于比一般人差,参政权的享有乃是平等平等,至于参选国代是不是谈说俗事,是不是等于亲近国王大臣?也有商榷余地。
其次,思想家梁漱溟也是反对佛教为现世所用,对太虚的人生佛教主张不以为然:
似乎记得太虚和尚在《海潮音》一文中要藉着‘人天乘’的一句话为题目,替佛教扩张它的范围到现世生活里来,又仿佛刘仁航和其他几位也都有类乎此的话头,……总而言之,佛教是根本不能拉到现世来用的,若因为要拉它来用而改换它的本来面目,则又何苦如此糟蹋佛教?我反对佛教的倡导,并反对佛教的改造。[15]
梁漱溟认为儒家‘专谈现世生活’,而佛教‘专谈现世生活以外的事’,恐怕不是今日一般佛教学者所能接受的看法。关于出世入世的分疏,印顺法师曾有一段论述:为了全心全力解脱生死而厌弃世间,对宗教的体验来说也许是有用的,但因而对其余一切异常淡漠,对现实人生(家庭、社会、国家)只是消极适应它,这在佛法普及民间而言至少是不够的、不足以适应的,‘面对这种不足以适应社会要求的佛教、圣者,而想起了佛教公认的、释迦佛过去修行的菩萨风范,以及释迦成佛以来为法为人的慈悲与精神,不免要对出世佛法,予以重新的估价。’因而涌现出世而入世的佛教,就是所谓的大乘佛教。[16]
佛教学者张曼涛,就是根据此一大乘佛教的精神,赞扬太虚法师是中国近两千年来的佛教史上,真正表现世出世入之大乘精神的第一人:
大师出于真正佛陀之菩萨心怀,握本执圭,安民安法,故其虽遭遇教内短见之士之反对,却仍然秉着虽万人吾往矣之精神,发表其僧侣参政之论。此在整个大师的思想中,固非一最重要之处,但我们从中国佛教传统的形式以观,则不得不惊奇此乃跃足千波,截断众流之见。由一向隐遁山林寺院之僧,一脚便倡踏入最烦人恼心的民主议会之堂,此设非有其卓越古今之思,真发菩提心者,曷能语此。[17]
印顺法师面对这一篇赞扬太虚的文章,唯恐‘僧伽参政’被当作是否入世、是否大乘精神的唯一判准,遂撰一长文予以批评,还提醒:‘人间一切正行,都可以利益众生,都是菩萨事业,都是摄化道场,都是成佛因行。菩萨利济众生,可以从政而不一定要从政。’[18] 印顺法师的借题发挥,或可使道理更圆融透辟,但张曼涛既已指出僧伽参政之论在整个大师的思想中‘固非一最重要之处’,而且只是‘僧众使用菩萨无量法门中的一法之一’,[19]
其实已经说得够清楚了。
三、从政府档案看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目前中华民国国史馆典藏之《内政部档案》共16421卷,其中有关民国佛教史料约有三百余卷,据学者侯坤宏的整理分析,这批档案除涉及文物维护、佛学院创设、社会救济有关者外,率多与寺产纠纷或庙产兴学引起的交涉有关。原来清末张之洞就有庙产兴学的主张,乃至政策,一九三一年以后可视为第二次庙产兴学风波。所谓风波而不是运动,乃因寺庙方面总是被迫、不是自发,其中要以地方政府包括县长、乡长、保甲强令提拨寺租,强占寺产,乃至毁寺逐僧最为常见,佛教方面则懂得写公文向内政部请愿、抗议,通常内政部方面会行文向地方政府纠正,反对将寺庙财产提充乡镇建设经费,主要考量应在安抚民心或维系起码的法治。
兹从国民政府档案中挑选几个具体的案例,比较深入地探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一) 甘肃省临潭县有一藏传佛教寺院‘嘛呢寺’,其僧纲马昂旺丹主于1924年逝世后,原应由嫡堂孙马辙霄承袭,因该孙年幼故由其师活佛马洛劄丹真江楚暂行代理,17年后(1941)这位代理僧纲圆寂,遂有‘家舍族长并民众大小各代表’再四妥协会商,共选马辙霄正式承袭嘛呢寺僧纲,该寺头目袁得忠等并将此结果向县长立案存查,县长聂迵凡则呈文给甘肃省政府请求‘俯准委任并祈颁发钤记,俾资管理而便统制’,省政府方面‘除令准委任并刊发木质钤记外’,行文内政部 ‘咨请查照备案’。[20] 本案显示县政府是最直接的主管机关,省政府与内政部也分别扮演一定的角色。
(二) 中央政治学校肃州分校于1935年成立后,商同地方当局借用西街武庙三义庙药王庙旧址,稍加修葺开学上课,后来学生班次增多,教室宿舍不敷分配,须扩充校址,乃呈请酒泉县政府按征用民地手续办理,但酒泉钟楼寺认为其寺产香火地二十余亩于1940年11月被该校‘恃强占用’,曾于1941年提起诉讼,经酒泉地方法院、甘肃高等法院第四分院判决所有权归钟楼寺,而1940年12月20日内政部地政司致礼俗司的一份公文指出,有关肃州分校用地归还钟楼寺问题,征收土地兴办学校原则并不违法,但肃州分校‘为直接承受中央管辖监督之学术机构’,依土地法第338条规定应由行政院核准,地价之补偿亦应依第377条之规定办理。不过,经法院判决之后该校仍逾限不还,于是1942年9月8日中国佛教会酒高安敦玉金鼎七县市分会乃电请重庆内政部‘俯准依法转咨归还或饬由该校在该县市区外照亩另购田地交还,以维产权,并请赔偿损失。’[21] 本案牵涉政府间(或政党间)争议,寺庙方面且能采取司法途径,惟该校仍逾限不还,可见司法的权威在当时仍隐而不彰;至于中国佛教会该‘七县市分会’请求内政部出面处理,结果如何限于资料不得而知。
(三) 河南省新蔡县金粟寺,原系清康熙年间宋祖法氏所捐赠之土地房屋改建而成,历经购地扩充颇有规模,但同治年间宋氏子孙企图‘化寺为祠’,强在寺内悬挂宋氏祠堂匾额一面,每年春秋岁时藉着扫祭而要求寺僧供应酒食,若干地方士绅不以为然;1929年宋氏族裔有一名垣忠号英俦者,担任河南省党部委员,乃乘省令‘废庙兴学’之际运作将金粟寺原有田产二千亩拨出一千五百亩筹办私立诞文小学,1940年12月20日该寺住持僧祥云透过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由佛教会理事太虚具名)向内政部行文要求保护寺产,翌年1月9日内政部咨请河南省政府‘查明核办、并希见复’,同月21日又有新蔡县公民刘擎伦等为宋垣忠‘藉兴学名义狡占金粟寺’,呈文内政部‘请饬彻查’,1941年6月2日河南省政府为该省新蔡县金粟寺纠纷回复内政部,所做的处置似乎对金粟寺不利:所有权确定问题属司法范围、1500亩给诞文小学之事照旧、寺僧祥云既然挑拨生事准予驱逐。不过,1942年3月又有新蔡县公民代表张山甫等向内政部呈请查办宋氏家族企图侵占金粟寺庙产的公文,[22] 可见寺院方面除了有佛教会的奥援,也需要一定的社会力(信众)的支持,才可能与省县政府做多年的拔河。
(四) 太虚法师曾经对中国佛教寺院之家族化、子孙化现象不以为然,但单凭佛教自身的力量势难改革,所以太虚针对裁汰僧侣、提升素质的事认为‘非政府主管机关以政治力量执行,亦难睹其成效。’[23] 太虚的期待似非全然空想,而有部分的事实基础。例如1936年9月11日,江苏省政府第1855号训令(摘录):‘令镇江县政府督饬佛教会迅速慎选适当之僧,即日到庵(镇江焦山碧山庵)接管,凡与岫奇有关之法派不得被选,以惩传子传孙之恶习,而树十方常住之先声。’镇江佛教会果然改派定慧寺僧玉泉为住持,碧山庵方面则有退居和尚柳溪等补呈文件,谓该寺向以薙度法派相传,不采选贤制度,例如柳溪继承善微,岫奇接任柳溪。此次岫奇因案去职,9月12日宝莲接任住持亦循此传统,而9月18日镇江佛教会所派定慧寺僧玉泉,并非碧山庵薙度法统,自不能接充碧山庵住持,故于1936年10月30日向内政部提起诉愿;该诉愿人亦无继承资格;同年9月20日柳溪提起再诉愿谓吸食鸦片系遭人挟嫌诬报、不能作为论据;其间由于岫奇、宝莲二人先后呈称本件诉愿案系假冒名义,声明无效,柳溪遂以单独名义表示不服提起再诉愿,内政部于1937年11月1日作成驳回之决定书,就从程序上认为‘无论原处分之内容有无违法或不当情事,与再诉愿之权益并无关系,更无损害之可言。’[24] 本案显示,省政府根据某种资讯和理念,即可训令县政府督饬县佛教会,改变某个寺院的住持,虽然形式上仍经过佛教会或可免除妨碍宗教自由之讥,但政治力强势介入的痕迹明显可见,而僧人柳溪懂得以诉愿、再诉愿的方法维护自己的利益,可以令人感受到中国佛教在1930年代的某种‘现代性’。
四、从《海潮音》杂志看佛教与政治的关系
1918年太虚法师在上海创办‘觉社’,作为其改革佛教的据点,当时出版《觉社丛刊》季刊计有五期,为配合弘法需要,于1920年2月改为《海潮音》月刊,这份刊物随着时局变迁曾在上海、武昌、重庆等不同地方编辑出版,历经善因、满智、法舫、芝峰、福善、尘空、大醒等等不同法师与居士负责编务,1949年迁移台湾继续出版,‘销数不过二千多份,可是读者却遍满了各省市及南洋各处’,[25] 可说是中国佛教迄今为止‘历史最久’的一份刊物,‘相当于一部近代佛教史,为佛教留下完整的纪录’。[26]
1948年负责《海潮音》编务的大醒法师曾说:‘我们(太虚)大师的两大慧命事业,一是武昌佛学院,二是《海潮音》月刊。(法)舫法师……既主持母院约近十载,同时他又为本刊主编有三次之多……。’[27]《海潮音》不但历史悠久,而且反映了太虚法师及其徒众的改革佛教事业,记载了数十年中国佛教的各种动态,自然可以从中看到佛教与政治的若干关系。
首先,来自各地的讯息显示,地方政府与佛教寺院或佛教会互动的情形不一,但觊觎庙产的企图相当普遍。例如1929年安徽省佛教会快邮代电:安庆市政筹备处拟订抽收本市僧道唪经‘迷信捐’章程,呈奉省府第94次委员会谈话会议议决照准,定本年12月1日开始征收;省佛教会遂决议一致反对,自12月1日一律停止应赴三日以示消极抵制,一面请愿省府覆议收回成命,一面呈请全国佛教会,转呈国民政府明令制止。[28] 又如1947年湖北省政府议决酌提庙产收益为教育经费,中佛会认为显与〈监督寺庙条例〉抵触,请内政部转咨撤销,省政府于10月21日发出公函谓:‘自应照办。除分令各县市政府将原经收管之寺庙财产一律发还,并依监督寺庙条例第十条之规定,商得各该寺庙住持僧之同意,将财产收益酌提一部兴办公益慈善事业……’。[29]
再如,1948年浙江定海、镇海县政府根据县参议会之议决,设经忏捐征收所,强迫佛教寺庵缴经忏捐;其实此捐早经中佛会于1930年呈奉国民政府批交行政院令行内政部,请转咨饬令撤销。[30]《海潮音》作为一份佛教刊物,除了记载、传达这类讯息,也会发出批判之声,例如针对1948年3月5日报载上海市参议会议决对于该市寺庙‘得由主管机关会同民意机关及地方公正士绅组织委员会整理之’,上海寺佛教分会认为‘显有侮视教会、侵犯宗教尊严,……殊与宪法相抵触。’大醒法师遂发表文章称许这样的驳论,还说‘今后正是实施宪政的时代了,宪法上给予我们有许多应享的自由权利,我们僧侣应该要自己争取!’[31]
不过,如果根据以上的事例,即作成‘民国佛教总是受到地方政府的压迫剥削’的单一结论,恐亦不合史实。例如湖南省宁乡有一大沩山密印寺(沩山寺),原有山田3,700余亩,以放佃收租作为寺院的收入来源,惟寺僧只有完粮收租之权,并无退佃之权,若佃房不种可自觅替人,寺僧不得干涉或收回,此制自唐代以来一无变更;1930年《海潮音》关于沩山寺有一则记载谓:佃户多至六百余家,人数既众良莠不齐,每多欺凌寺僧,欠租抗粮、因循积习,终于酿成 1918年‘匪佃’放火戮僧之惨祸。沩山寺僧所能采取的对策,除了谆谆告诫、晓以因果,或召集团甲转谕各佃不得借端刁抗以外,还可以向宁乡县长刘裔彬求援:‘以后该沩山佃户如仍有短租情事,一经该寺僧呈诉,即请拘案追缴,刘县长亦允依法维持。’[32] 可见,佛教寺院也有仰赖地方政府‘保护’以维持生计的一面。
从中央政府的层面看,民国时期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确有一定程度的亲佛环境,一位作者如此描述:‘现政府中之重要领首,皆多信佛。如国民政府主席林子超氏,即笃信佛教;司法院长居觉生氏,亦甚信佛。即军事领袖蒋介石氏,亦极爱护佛教。’[33] 其中,所谓蒋介石爱护佛教,应与太虚法师有关,即1927年9月蒋氏电邀太虚游奉化雪窦寺,两人长谈竟日、相偕游千丈岩,时逢中秋赏月,太虚又为蒋氏夫妇(蒋经国之母)等略说心经大意。印顺法师就此评论道:‘国民政府下之佛教,得以从狂风暴雨中复归安定,得以泄沓混日,确与此夜此人有关。’[34] 再者,1932年10月8日,太虚应蒋氏延请,任奉化雪窦寺住持,行进院礼,[35] 此后数年太虚在该寺开讲《出生菩提心经》、《弥勒上生经》、《解深密经》等多部经典,并曾设药师法会,祝蒋五秩之庆。[36] 此外,中高层的军政人物也不乏护持佛教的事例,如1932年世界佛学苑汉藏院正式开学,由重庆佛学社向国民革命军第廿一军司令部‘呈请拨款’,军长刘湘准于省教育经费项下,按月拨助洋600元,以资进行;[37] 同年的《海潮音》也曾记载,武昌佛学院董事会欢迎徐督办克成、夏司令灵柄为‘院护’云云。[38]
佛教界基于信仰的立场以及自身能力考量,曾在中日战争期间组织僧侣救护队,参与‘救死护生’,[39] 平常则启建法会以祈求国泰民安,例如1931年11月26日迄1932年5月25日,长沙启建半年的水陆道场,以超渡全国阵亡将士;[40] 1932年10月21日,北平雍和宫启建三天的时轮金刚法会,虽尝被讥为‘经咒救国’,但法舫法师认为这是1932年全国佛教五项重要的成绩之一。[41]
不过,透过私人情谊或以法会消灾祈福,不足以构成制度化的、现代化的政教关系。尤其国共内战方殷,共产党势力日趋壮大之际,前述坐拥田产收取地租的寺院经济模式,自然受到教内有识之士的检讨,1948年善因、大醒就撰文呼吁全国各寺院,只要有田土可耕、有山林可植,就应添些农具耕牛,收回土地自耕,既可不受饥饿之苦、不受外界之摧残,又可加政府之保障,‘但应留点慈念,对于每一佃农所耕之田,只宜收回半数或一部份来自耕,毋使旧佃完全失业,以符佛心。 ’‘与其替斋主做经忏,不如自食其力。’[42] 另一位作者也说:‘僧伽应根据《郁单越国经》所说的佛教的社会主义或民生主义,想出切实的办法,付诸实行,以求达到目的。’[43] 对于国共内战,则有人从佛教的观点提出批判:‘谁都知道内战发生的原因,是两个党因为互争政权而生起的。’‘双方都把党的利益高置于人民的利益之上,都在驱赶着善良的人民做着民族自戕的蠢事。’内战发生的主因既然是两党的自私性,‘去私’便是和谈成功的首要条件。[44] 道理虽然讲得不错,但是对于客观决定的结构、江河日下的局势,显然无济于事。
五、讨论与结语
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在神学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解放神学家认为,神学主要是要对实际的生活提出批判、反应与思考,他们使用的方法可归纳为四点: (一) 主张‘历史的实践’,(二)‘历史的情况’是神学思考的出发点,有别于过去以圣经或启示为出发点,(三) 藉助社会科学的方法来了解历史实际情况,(四) 神学思考必须采用某种意识型态,一般解放神学家率皆主张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包括采用依赖理论(theory of
dependence)来了解拉丁美洲的实况。以上第四点最容易引起争议,解放神学家的理由是:信仰必需意识型态来作媒介,否则会与历史实况脱节、会成为死的信仰。[45] 然而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神学思考如何与无神论相协调?会不会喧宾夺主?不论是选择性地使用圣经,或选择性地采用马克思主义,选择的根据何在?俱是问题。
佛教方面不容易找到可与解放神学相比拟的思想,勉强说,泰国的佛使比丘(1906-1993)有接近之处,佛使认为宗教与政治有基本的关连,真正的政治是用来对治邪知、邪见、贪爱烦恼和类似的弊病;社会科学本质上就是一种道德,因为它的目的是解决社会所有的问题,使社会和谐、平衡。佛使还认为理想的民主政治是‘如法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它必须限制个人自由,必须采用‘独裁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例如阿育王的政治制度就是一种全然‘独裁的’社会主义,他驱逐僧伽中的外道人士,并严格要求所有阶层百姓的行为都要端正,他是一位为全体福利着想的君主。[46] 虽然佛使比丘对社会主义的定义特殊,把它当作相对于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而言,或有自圆其说的可能,但在二十世纪鼓吹独裁的方法,毕竟不合时宜。
不过,解放神学家所谓‘历史的情况’、‘社会科学的方法’则很值得重视,本文企图从国民政府的内政部档案,以及从《海潮音》月刊入手,就是要究明 1912~1949年之中国的历史实况。大率归纳而言:(一) 不论在清末、北洋政府或南京政府时代,都有庙产兴学或课征迷信捐、经忏捐的倡议,可见在政治因素之外,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容忽视;(二) 比较而言,地方政府的苛扰比中央政府严重,中央方面的亲佛环境则是因为首长信佛或如太虚、蒋介石的私人关系,并非制度性的保障;(三) 《海潮音》也曾记载,县长派兵协助佛教寺院向佃户收租的情形,可见不能做成民国时期‘政府迫害佛教’的简化结论;(四) 佛教方面常举办护国息灾法会、超渡阵亡将士法会,抗日战争期间努力发挥‘救死护生’的角色,整体而言是采取支持(拥护)政府的立场;[47] (五) 佛教徒已经懂得透过立法、透过组织教会,甚至个别地以诉愿、再诉愿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惟全国性的教会频生波折,部分的因素来自教内的派系纷争。此外,关于僧伽参政的问题,虽曾受到教内教外人士的质疑,笔者认为主要的困难不在于理论、不在于有否经说的依据,而在于实际上佛教界有没有整合的机制以提出具代表性的候选人?在于佛教界对当下的政治外交经济文化诸问题能提出什么‘如法的’主张?
理论上孰为理想的政教关系,近年来已有学者强调‘政教制衡’而非‘政教分立(离)’,更非‘政教合一’,笔者同意政教制衡的确比较切合实际且符合民主之理,亦即政治与宗教之间可以互相支持也可以互相反对,只要遵守‘不过份连结’(non-excessive
entanglement)和‘非歧视性’(non-discrimination)两个原则即可。[48] 昔日太虚法师关于淘汰僧尼、整建僧会的目标曾经寄望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今日看来当知不切实际,而全国性的教会也不足以作为佛教现代化的首要指标,观乎今日中国大陆虽有‘中国佛教协会’,不见得即能发挥佛教的主体性,很多时候只是政治控制的一环。可见佛教现代化的问题,也要放在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来看,佛教毕竟是国家社会的一环,理想的政教关系只有在政治民主、社会健全的环境下才可能产生。因而佛教界对于国家社会的民主进步、公平正义如果不能扮演推手,至少也不应是旁观者或是向下拉扯的角色,所以个人认为,太虚法师不避政僧之讥,勇于对社会主义、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乃至具体的公共事务发言,犹应是今日佛教徒应该重视的榜样。最后,已故佛教学者傅伟勋教授的一段话,很适合作为本文的结尾:
我衷心盼望现代佛教徒以及佛教团体能够更积极地参与世间世俗的政治活动与社会工作,把大乘佛法的菩萨道精神真正带到我们人间的日常生活之中。佛教团体必须能够提出有助于社会福利与进步的建设性主张与措施,必须敢于提出有佛法根据的政见,也必须好好利用时机,在民主自由而多元开放的公开讨论条件下,正面提出具有说服力的佛教看法。……无论如何,奉持佛法的现代人不能再像过份保守的传统佛教那样,隔断佛法与世法,漠视世法,只管佛法。真正的佛法必须在从事于世法的改善转化的奋斗过程当中彰显出来,这是根据二谛中道产生的关涉佛教伦理本身应有的实践态度。[49]
【注释】
[1] 近年中国大陆出版品则有改变的现象,例如赵匡为主编,《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教关系》(第一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年),已处理到日、韩、泰、缅等国。又如宋立道,《神圣与世俗:南传佛教国家的宗教与政治》(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综论佛教与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关系。
[2] Ian Harris, ed., Buddhism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 Pinter, 1999), Preface, p. viii.
[3] 或称‘薄弱的宗教心’,见胡适,〈三论信心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07号(1934年7月1日),页2-6。
[4] 用美国学者史丹利.外因斯坦(Stanley
Weinstein)的话说,唐朝早期的帝王对佛教采取的是‘权宜的护持伴随着渐趋严峻的控制手段’。见氏着,释依法译,《唐代佛教:王法与佛法》(台北:佛光文化公司,1999年),页6。
[5] 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75。
[6] 李时友,〈中国国民党训政的经过与检讨〉,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八辑‘十年建国’(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页24。
[7] 以下大事整理自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页35-56;印顺,《太虚大师年谱》(台北:正闻出版社,1992年修订一版)。
[8] 太虚法师,〈建设适应时代之中国佛教〉,《太虚大师全书》(台北:太虚大师全书影印委员会,1956年初版,1970年再版),第35册,页4。
[9] 陈仪深,〈太虚法师的政治思想初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期(1990年6月),页279-298。
[10] 太虚法师,〈精诚团结与佛教之调整〉,《全书》第34册,页634。
[11] 太虚法师,〈上海市庙产注册事件〉,《全书》第34册,页641、642。
[12] 太虚法师,〈僧伽与政治〉,《全书》第35册,页180-183。
[13] 欧阳竟无,〈辨方便与僧制〉,收入洪启嵩、黄启霖编,《欧阳竟无文集》(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页219-228。
[14] 印顺,《太虚大师年谱》,页406。
[15]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台北:问学出版社,1977年),页210-211。
[16] 印顺,〈谈入世与佛学〉,收入《无诤之辩》(台北:作者出版,1976年),页182-183。
[17] 张曼涛,〈太虚大师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之地位及其价值——为纪念虚大师上生二十周年而写〉,收入氏着《佛教思想文集》(台北:狮子吼杂志社,1969年),页212-230。
[18] 印顺,〈谈入世与佛学〉,同前,页200。
[19] 详见张曼涛,〈读‘谈入世与佛学’后〉,前揭书,页154-211。[20] 国史馆藏《内政部档案》,(档号待查):甘肃省政府咨(内政部查照准临潭县政府)请委任马辙霄为临潭县嘛呢寺僧纲(1941年2月20日)。
[21] 国史馆藏《内政部档案》,128/1602:行政院交议有关中国佛教会酒高安敦玉金鼎七县分会代电请饬令中央政治学校肃州分校归还酒泉钟楼寺地产案(1940年12月13日);128/1605:中国佛教会酒高安敦玉金鼎七县分会电请依法转咨饬还钟楼寺产(1942年9月8日)。
[22] 国史馆藏《内政部档案》,档号待查:河南省政府为该省新蔡县金粟寺纠纷咨内政部(1941年6月2日);河南省新蔡县公民代表张山甫等呈请查办该县宋氏家族企图侵占金粟寺庙产乙案(1942年3月)。
[23] 太虚法师,〈建设现代化中国佛教谈〉,《全书》第33册,页278。
[24] 国史馆藏《内政部档案》,128/1621:江苏镇江焦山碧山庵僧人柳溪等不服江苏省府所为行政处分提起诉愿(1936年10月16日);(档号待查):内政部决定驳回江苏镇江焦山碧山庵住持纠纷再诉愿案(1937年11月1日)。
[25] 大醒,〈为本刊迁移台湾讲几句话〉,《海潮音》第三十卷第六期(1949年6月)。
[26] 于凌波,《中国近代佛门人物志》(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年),页245。
[27] 大醒,〈欢迎法舫法师归国〉,《海潮音》第廿九卷第六期(1948年6月)。
[28] 〈安徽省佛教会快邮代电〉,《海潮音》第十一卷第一期(1930年1月)。
[29] 〈中佛会会报〉,《海潮音》第廿九卷第一期(1948年1月)。
[30] 《海潮音》第廿八卷第十二期(1947年12月)。又参见大醒,〈镇海发生县税稽征人员捣毁寺庵事件〉,《海潮音》第廿九卷第十一期(1948年11月)。
[31] 大醒,〈我们不承认有干涉寺政寺产之任何名义的组织〉,《海潮音》第廿九卷第五期(1948年5月)。
[32] 〈陈委员严华为沩山寺自呈覆省政府及民政厅文〉,《海潮音》第十一卷第二期(1930年2月)。同期有〈罘月致太虚函〉谓县政府派兵四员协助催租,也是保护佛教云云。
[33] 谭云山,〈中国佛教现状〉,《海潮音》第十五卷第九期(1934年9月)。
[34] 印顺,《太虚大师年谱》,页240。
[35] 同上注,页347。另据谈玄法师(1937年奉太虚之命赴雪窦寺代理)的说法,并非‘应蒋氏延请’,而是1932年雪窦寺住持朗清以太虚与最高领袖相友善,遂率寺众并商同诸山及溪口镇绅,公请太虚来寺住持。见国史馆藏,《内政部档案》,128/1686:谈玄僧呈请驱逐劣僧案。
[36] 印顺,《太虚大师年谱》,页414。
[37] 《海潮音》第十三卷第八期(1932年8月)。
[38] 《海潮音》第十三卷第四期(1932年4月)。
[39] 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页276。又,有关中国佛教在抗战期间的表现,详见乐观法师,《中国佛教近代史论集》(台北:作者出版,1978年),页23-99。
[40] 《海潮音》第十三卷第六期(1932年6月)。
[41] 《海潮音》第十三卷第十二期(1932年12月)。另外四项是宋版藏经影印、世界佛学苑设立、河南省佛教学苑设立、重兴洛阳白马寺。
[42] 善因、大醒,〈赞成僧作自耕农〉,《海潮音》第廿九卷第十二期(1948年12月)。
[43] 伍薏农,〈我们往那里住?——36年在厦门寿山岩讲〉,《海潮音》第廿九卷第四期(1948年4月)。
[44] 石孚,〈从无我大悲的观点看和平运动〉,《海潮音》第三十卷第三期(1949年3月)。
[45] 慕理诺(Miguez-Bonino)等着,《基督教与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台北:台湾神学院,1995年),廖涌祥牧师引言,页15-29。
[46] 佛使比丘(Buddhadàsa Bhikkhu)着,香光书乡编译组译,《法的社会意义》(嘉义:香光书乡出版社,1996年),页86、87、90、100。
[47]
曾有学者归纳,宗教团体对政府采取的态度可有四种类型:支持,中立,以社会为立场、为社会作见证,公然对抗。无疑,民国时期的佛教属第一种。参见Murray
A. Ribinstein, ' Patterns of Church and State Relations in Modern Taiwan ', 收入《中国近代政教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淡江大学,1987年),pp.359-374。
[48] 参见郭承天,《政教的分立与制衡》(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2001年)。
[49] 傅伟勋,〈(大乘)佛教伦理现代化重建课题试论〉,收入氏主编《从传统到现代——佛教伦理与现代化社会》(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年),页233-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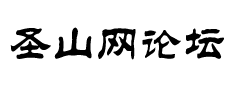

 发表于 2020-6-19 06:48:17
发表于 2020-6-19 06:48:17